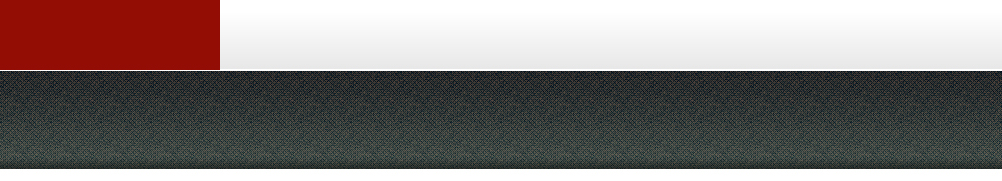傲世皇朝平台共读《双城记》7胡狼与狮子的酒宴。导读:《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所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情节感人肺腑,是世界文学经典名著之一,故事中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结起来,围绕着曼马内特医生一家和以德法日夫妇为首的圣安东尼区展开故事。小说里描写了贵族如何败坏、如何残害百姓,人民心中积压对贵族的刻骨仇恨,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法国大革命,本书的主要思想是为了爱而自我牺牲。书名中的双城指的是巴黎与伦敦。
本次共读将带领大家阅读《双城记》第二部分的第4和第5章,字数8千字左右,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读完记得在本文底下留言作为签到,留言要超过十个字且要在当天留言才有效哦。12月的共读到此结束啦,请大家准备纸书或者电子书继续阅读《双城记》,阅读原文附有购买链接哦。
在法庭里沸沸扬扬地泡了一整天的人们,连最后那几个,都穿过灯光昏暗的过道,走得一干二净了。这时,马奈特医生、他女儿露西·马奈特、洛瑞先生和被告辩护律师斯特里弗先生,一起围站在查尔斯·达内先生的周围——他刚刚获释——庆贺他死里逃生。
哪怕在比这亮得多的灯光下,也很难认出这个一脸智力超群、身姿挺拔的马奈特医生,就是巴黎阁楼上的那个鞋匠。可是无论是谁,即使没有机会对他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即使没有听过他悲怆低沉的语调,也没有见过那无端地笼罩着他的茫然神情,只要朝他看上一眼,就没有人会不再看他的。一种外在的原因,比如提到他多年来遭受的苦难,就经常会——像刚才被传讯时那样——从他灵魂深处勾出那种茫然的神情,当然它们也会自行浮现出来,给他蒙上一层阴影,使那些了解他身世的人难以理解。仿佛看见夏日的阳光,把远在三百英里外的巴士底狱的阴影,投射在他的身上。
只有他的女儿有力量从他心中驱除阴郁的忧思。她是一条金线,把他受苦遭难前的“过去”和受苦遭难后的“现在”连接了起来,她的语声,她的容光,她的抚爱,几乎总是能对他产生强大有益的影响。当然,她的魔力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她记得有几次连她也无能为力。不过这种情况为数不多,也无关紧要,她相信以后不会再有了。
达内先生满怀感激之情,热烈地吻了她的手,接着转身向斯特里弗先生衷心致谢。斯特里弗先生三十刚刚出头,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要大二十岁。他身材粗胖,声音洪亮,红光满面,直来直去,从不拘泥于斯文礼节。在人们聚谈时,他总是喜欢排开众人挤到前面去(在精神上和行动上都是如此),抢先插话,这正好说明他在实际生活中那种敢闯敢上的冲劲。
这时他仍然戴着假发,穿着律师袍,挺胸凸肚,站在他的当事人面前,把个纯朴老实的洛瑞先生都挤到了一边。他说:“达内先生,我很高兴能把你体体面面地解救出来。对你的起诉实在太卑鄙了,卑鄙到了极点,不过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
“我使出了全身本领来救你,达内先生;我相信,我的本领也跟别人的一样大。”
这很清楚,他是要人义不容辞地出来说声“你的本领大多了”,而洛瑞先生也确实这样说了。他这样说,也许并非完全出于无私,而是想趁机挤回原地。
“你这样看吗?”斯特里弗先生说,“对了!你在这儿整整待了一天你应该最清楚,再说你也是个代人办理事务的。”
“正因为是这样,”洛瑞先生说道,这时,那位精通法律的律师像刚才把他挤到一边那样,又把他推回到这伙人里面,“作为代理人,我要求马奈特医生宣布结束这场谈话,命令我们各自回家。露西小姐看来不太舒服,达内先生担惊受怕了一天,我们大家都累坏了。”
“你说的只能代表你自己,洛瑞先生,”斯特里弗先生说,“我可还得工作一个通宵哩。你说的只能代表你自己。”
“我代表自己说话,”洛瑞先生回答说,“也代表达内先生,露西小姐,还有——露西小姐,难道你不认为我可以代表我们大家吗?”他对着她直接提出这一问题,并且朝她父亲看了一眼。
她父亲变得脸色发呆,用一种非常奇特的目光望着达内,目光死死盯着,双眉紧皱,现出厌恶和信不过的神色,甚至还夹杂着几分恐惧他带着这种令人难解的表情,神志又陷入了茫然。
被释犯人的朋友们以为,这天晚上他是不会被释放了——这印象是他自己造成的——于是都各自散去。过道里的灯差不多全都熄灭了一扇扇铁门也都砰砰关上,这阴森森的地方变得空无一人,要到明天早上,大家对绞刑架、示众枷、鞭笞柱和打印烙铁的兴趣,才会重新使这儿人山人海。露西·马奈特走到她父亲和达内先生中间,到了门外。他们叫来一辆出租马车,父女俩坐上车先走了。
斯特里弗先生在过道里和他们分手后,便冲回法庭的更衣室去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刚才没有跟他们聚在一起,也没有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搭讪过一句,只挑了个阴影最浓的墙角站着。这时,他默不作声地跟着大家走了出来,站在那儿,一直看着马车离去,然后才走向站在人行道上的洛瑞先生和达内先生。
没有人知道卡顿先生在这天的审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没有人对他表示感谢。他已经脱去律师袍,可那外表并没有因此好了多少。
“要是你知道公事人善良本性的冲动和公事公办的外表发生冲突时,内心斗争是何等激烈,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达内先生。”
洛瑞先生脸红了,诚恳地说:“这一点你以前已经说过了,先生。我们这些替银行办事的人,是身不由己的。我们不得不首先为银行着想,然后才能考虑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卡顿先生漫不经心地答道,“别见怪,洛瑞先生。我毫不怀疑,你跟别人一样好;我敢说,你比别人更好。”
“说实在的,先生,”洛瑞先生没有理会他,顾自往下说,“我实在不明白,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请原谅,我比你虚长几岁,所以也就冒昧这么说了。我真的不明白,这和你的公务有什么关系。”
“好啦,先生!”洛瑞先生被他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弄得火冒三丈,叫了起来,“公务是件好事,是件非常体面的事情。再说,先生,如果是公务逼得人隐忍克制,不能随便说话,不能为所欲为,那么像达内先生这样一位宽宏大量的年轻绅士,一定会懂得如何去体谅别人的这种处境的。达内先生,晚安,上帝保佑你,先生。我想你今天大难不死,日后必有后福。——来轿子!”
不仅对这位律师,也许对自己也有点生气,洛瑞先生匆匆上了轿子,径直回台尔森银行去了。卡顿满身葡萄酒气,显得不太清醒,这时哈哈大笑起来,转身对达内说:
“你我碰在了一起,这真是个奇妙的缘分。现在,你和跟你长相一样的人一起站在这街心石头上,你一定觉得这是个很不寻常的夜晚吧?”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方才你在黄泉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你说话好像有气无力的。”
“那你干吗不去吃点东西?我在那伙傻瓜讨论你究竟应该属于哪个世界——阳世还是阴间时,就已经吃过饭了。让我带你到离这儿最近的一家酒馆去好好吃上一顿吧。”
他伸出手去挽住对方的胳臂,领他走下拉盖特山,来到弗利特街走过一段盖有天篷的路,进了一家酒馆。他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查尔斯·达内饱餐了一顿,又喝了些好酒,很快就恢复了体力。卡顿和他同坐一桌,在他对面,也摆着一瓶葡萄酒,他对达内也是那副半似傲慢的满不在乎的态度。
“有关时间和空间,我脑子里还是一片糊涂,不过现在好多了,已经有了人世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忘掉我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没有一点用处——像这样的酒除外——我对它也没有用处。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俩不太相像。说实在的,我渐渐觉得,我们俩,你跟我,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太相像。”
查尔斯·达内被这惊心动魄的一天弄得丧魂失魄,觉得和这个跟自己相像、举止粗鲁的人坐在一起恍如梦中,他茫茫然不知如何回答,于是就干脆不作回答了。
“现在你已经吃完饭了,”卡顿过了一会儿说,“为什么不干一杯呢达内先生?怎么不祝杯酒?”
卡顿干杯的时候,两眼直盯着他朋友的脸,随后他把酒杯朝背后一掷,杯子在墙上碰得粉碎。接着,按了按铃,另要了一只。
“那位在黑暗中扶上马车的小姐真漂亮,达内先生!”他说着,又把新拿来的高脚杯斟满。
“那个怜悯你,为你流泪的,可是位漂亮小姐啊!感觉怎么样?能得到这种同情和怜悯,即使受到性命攸关的审判,也是值得的吧。是不是,达内先生?”
“我把你的口信传给她,她听了非常高兴。当然,她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我看得出。”
这么一说,倒使达内及时想起,这位令人不快的伙伴在今天的危难中,曾经主动帮助过他。于是他把话题转到了这一点上,为此向他表示感谢。
“我不需要任何感谢,也不值得别人感谢,”这就是他漫不经心的回答,“第一,这算不了什么;第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达内先生,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实在的,卡顿先生,”对方非常窘迫地回答,“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达内一面站起来按铃,一面说,“我希望这不会妨碍我叫人来结账,也不妨碍我们双方都不怀敌意地分手。”
卡顿答道:“一辈子都不会!”达内按铃。“全部账都你付吗?”卡顿问,在对方做了肯定的回答后,他又说:“那就再给我拿一品脱这种酒来,酒保,到十点钟时来叫醒我。”
付完账,查尔斯·达内站起身来,向他道了晚安。卡顿也站了起来,但没有道晚安,而是带着一副咄咄逼人的神情说道:“最后再问一句,达内先生,你认为我喝醉了吗?”
“那你同样还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是个失意的苦工,先生我不关心世上的任何人,世上也没有任何人关心我。”
“也许是这样,达内先生;也许并非如此。别因为你头脑清醒就自鸣得意了,你还说不准它可能会落到什么地步哩。晚安!”
当这位怪人剩下独自一人时,他拿起一支蜡烛,走到墙上挂着的一面镜子跟前,仔细地把自己打量了一番。
“你特别喜欢那个人吗?”他喃喃地问镜中的自己,“你干吗要特别喜欢一个跟你相像的人呢?你身上并没什么可喜欢的,这你自己知道啊,你这个混蛋!看你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你喜欢上这个人自有你的道理,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你堕落前的模样,你本来可以成为什么样子!跟他对换一下,你是否也会像他那样受到那对蓝眼睛的青睐像他那样得到那张激动的小脸蛋的怜悯呢?说下去呀,干干脆脆地说出来吧!你恨这个家伙!”
他向那一品脱酒寻求安慰,几分钟之内就把它喝得一干二净,随即就伏在手臂上睡着了,他的头发披散在桌子上,那像长长的裹尸布般的烛泪,滴落在他的身上。
那是纵酒的岁月,多数人在狂饮无度。打那时以来,时光老人已经使这种风习起了很大变化。如果在无损于其绅士声誉的情况下,我们把当时一个人一夜之间所灌下的酒如实加以报道,在今天看来,就会觉得是荒诞不经的夸张。在嗜酒方面,博学的法律界当然也不会自甘落后于其他各界。那位冲劲十足、业务兴隆、财源茂盛的斯特里弗先生,也如在法律界进行的其他竞争一样,在这方面绝不会落后于他的同僚。
斯特里弗是老贝利的宠儿,也是民事治安法庭的红人。他已经小心谨慎地爬上了飞黄腾达之梯的最低几级。如今,民事治安法庭和老贝利都不得不特意召唤这位大红人,投入他们那急不可待的怀抱,因而每天都可以看到斯特里弗先生那张红光满面的脸儿,从一片花坛似的假发中冒出,极力迎向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尊颜,像一株硕大无朋的向日葵,朝着太阳,突出在满园争艳的群芳之上。
律师界的人一度认为,斯特里弗先生固然能言善辩,无所顾忌,机敏灵活,敢作敢为,但他没有从大量材料中取其精要的才能,而这是一个辩护律师至为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条件。可是后来,发现他在这方面有了显著进步。他的业务愈兴隆,他把握精要的本领似乎变得愈大。不论他晚上和西德尼·卡顿先生对饮到多晚,第二天早上,他准能把自己的论点准备得有条有理。
吊儿郎当、前途无望的西德尼·卡顿,是斯特里弗最得力的助手。每年从希拉里节开庭期到米迦勒节开庭期,这两个人在一起喝下的酒,足以浮起一艘皇家兵舰。斯特里弗不管在哪儿办案,都有卡顿跟着,而这位助手,总是双手插在口袋里,两眼直望着法庭的天花板。他俩一同
去参加巡回审判,甚至在巡回途中,也依旧酣饮到深夜。谣传有人看见卡顿大白天喝得踉踉跄跄,像只浪荡耽乐的猫儿,偷偷溜回自己的寓所。后来,关心此事的人们纷纷议论说,西德尼·卡顿虽然成不了狮子,却是只极好的胡狼,甘居卑位,对斯特里弗竭尽忠诚。
“十点了,先生,”酒店侍者按照卡顿事先的吩咐,前来叫醒他。“已经十点了,先生。”
他感到很困,昏昏然又想睡去,可那侍者却非常机灵,哗啦哗啦捅了足足五分钟的火炉,弄得他只好站起身来,把帽子往头上一扣,走出门外。他拐进圣堂区,在高等法院和纸楼之间的人行道上来回走了两趟,然后才转身进入斯特里弗的事务所。
斯特里弗的书记员从来不参加这类讨论,早就回家了,是斯特里弗亲自来开的门。他穿着拖鞋,披着件宽松的睡袍,为了舒适还敞开领口。他的眼睛周围有一圈放纵、倦怠、枯焦的印记,凡属他这类嗜酒贪杯的人脸上,都有这样的眼圈。从杰弗里斯的画像起,所有纵酒时代画像上的人物,虽然经过各种艺术加工,仍然能找到这种痕迹。
他俩走进一间昏暗的屋子,四周摆着书,到处扔满废纸,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炉架上一把水壶呼呼地冒着热气,在乱七八糟的废纸堆中,一张桌子闪着光亮,桌子上摆着许多葡萄酒,还有白兰地、朗姆酒、糖和柠檬。
“多亏你想出个好点子,西德尼,提出个面貌相像的问题。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的?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我觉得他是个挺英俊的家伙,我想,要是走运的话,我多半也该是这个样子。”
胡狼绷起脸,解开衣服,走进隔壁房间,拿来一大壶冷水,一只脸盆,还有一两条毛巾,也把毛巾浸在水里,拧到半干,叠起放在头上,样子难看极了,随后他坐到桌边,说道:“开始吧,我准备好了!”
于是,狮子怡然自得地仰靠在酒桌一头的沙发上,而胡狼则坐在堆满文件材料的另一头酒桌旁,酒瓶和酒杯也近在手边。两人都毫无节制地不时伸手到酒桌上拿酒喝,只是姿势不同罢了:狮子多半是靠在沙发上,双手插在腰带里,望着炉火出神,或者随意翻阅一下那些不太重要的文件;胡狼则紧锁双眉,聚精会神地埋头伏案工作,就连伸手去拿酒杯时,眼睛也不抬一下——常常要摸上好一会儿,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有两三回,事情实在太棘手了,胡狼不得不站起身来,重新把毛巾浸湿。光顾过水壶和脸盆后回来时,他头上缠着湿毛巾,样子古怪得难以形容,加上那一脸严肃焦急的神情,更加显得滑稽可笑。
最后,胡狼终于为狮子调制出一份紧凑的美餐,走上前去奉献给大王。狮子小心谨慎地接了过去,在胡狼的帮助下,自己又作了一番选择,加上几句评语。经过反复讨论,狮子又把双手插进腰带,靠在沙发上沉思默想起来。为了提神,胡狼在喉咙里灌下一大杯酒,又去换了一把冷毛巾,然后着手调制第二份菜肴。这份菜肴做好后,又用同样方式拿去奉献给狮子大王,直到凌晨三点才大功告成。
胡狼从头上摘下那块一直在冒热气的湿毛巾,抖了抖身子,打了个呵欠,还打了个冷战,照斯特里弗说的干了一大杯酒。
“老什鲁斯伯里学校的老西德尼·卡顿,”斯特里弗摇头晃脑地历数着卡顿的过去和现在,“还是那个跷跷板一样的西德尼·卡顿,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精神饱满,一会儿垂头丧气。”
“唉!”另一个叹了一口气,回答说,“是呀!还是同一个西德尼还是同样不走运。就是在那会儿,我也老给别人做作业,很少做自己的。”
“卡顿,”他的朋友神气活现地对他摆起架势,站在他面前,仿佛那火炉是个能炼出持久努力的熔炉,他正准备做件好事,把老什鲁斯伯里学校的老西德尼·卡顿推进炉门去炼上一番,“你那条处世之道,永远是条蹩脚之道。你既鼓不起干劲,又没有目标。你瞧瞧我吧。”
“照我看来,部分是靠雇用我的缘故吧。不过在这方面,你来教训我就像教训空气一样,你花的时间实在不值得。你自己要干什么,你就干去。反正你老是占先,而我总是落后。”
“我没有参加你的诞辰盛典,不过我认为你是天生的富贵命。”说到这里,卡顿笑了起来,于是两人都笑了。
斯伯里以后,”卡顿继续说,“你总是占你的先,而我,总是落我的后。甚至在巴黎学生区同学那时,你们在一起学法语,学法国的法律,还有那些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的杂七杂八的法国玩意儿时,你就处处得手,而我总是处处——落空。”
“凭良心说,我不能肯定这不是你的错。你总是不断地钻呀,冲呀,挤呀,推呀,无休无止,弄得我毫无进取的机会,只好在一旁发霉生锈。不过,在这种天快要亮的时候谈论一个人过去的事,未免太煞风景了。在我离开之前,还是换个话题,说点别的吧。”
“好吧!那就为那位漂亮的女证人干杯吧。”斯特里弗举杯说道,“这下你该高兴了吧?”
“漂亮的女证人,”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杯子嘟囔道,“今天一个白天,还有晚上,我已经见够证人了,你说的漂亮的女证人是哪一个呀?”
“整个法庭都倾倒!谁让老贝利来判定美丑的?她只不过是个金发玩具娃娃罢了!”
“你知道吗,西德尼?”斯特里弗用锐利的目光望着他,用一只手在红光满面的脸上慢慢地抹了一把,说道,“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你很同情那个金发玩具娃娃,而且你很快就发现她出了事。”
“很快发现出了事!要是一个姑娘,管她是玩具娃娃或者不是玩具娃娃,在一个男人鼻子底下两三码远的地方晕过去,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的。好,我跟你干杯,可我并不觉得她漂亮。我现在不想再喝了,我要去睡觉了。”
当主人拿着一支蜡烛,把他送到楼梯口,照着他下楼时,黎明已经冷冷地从积满污垢的窗户透了进来。他走出门外,迎面扑来悲凉的空气,天空阴沉沉的,河水黑森森的,整个景象犹如一片毫无生气的荒漠。阵阵尘埃在清晨的疾风中团团飞旋,仿佛荒漠中的飞沙在远处腾空卷起,前锋已经开始弥漫这个城市。
浑身是无用的精力,周围是空旷的荒漠,他在穿过一条僻静的小巷时,收住了脚步。霎时间,他看到眼前出现了一片崇高志向、克己为人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构成的海市蜃楼。在这幻景中的美丽城市里有着无数虚无缥缈的亭台楼阁,娇媚可笑的人儿从那儿朝他频送秋波花园里熟透了的生命之果累累垂枝,希望之泉在他眼前粼粼闪光。可是刹那之间,这番幻影就消逝无踪了。他走进一群楼房的天井,爬上一间高高的阁楼,和衣倒在一张凌乱不堪的床上,无用的泪水濡湿了床上的枕头。
太阳悲悲切切、切切悲悲地冉冉升起,它所照见的景物,再也没有比这个人更悲惨的了。他富有才华,情感高尚,却没有施展才华、流露情感的机会,不能有所作为,也无力谋取自己的幸福。他深知自己的症结所在,却听天由命,任凭自己年复一年地虚度光阴,消耗殆尽。